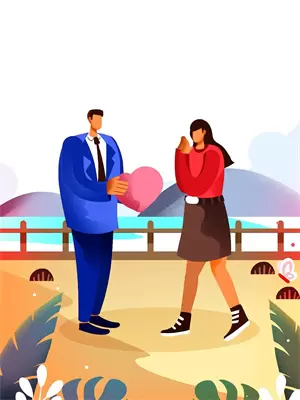篡改生辰八字
作者: 陈文序其它小说连载
其它小说《篡改生辰八字讲述主角周慕云星辰的爱恨纠作者“陈文序”倾心编著本站纯净无广阅读体验极剧情简介:1987年青州钢铁厂家属院我蜷在筒子楼外的垃圾堆改锥捅进收音机后盖手指关节冻得发父亲躺在三楼那张嘎吱作响的铁架床右腿石膏里渗出黄褐色的昨晚他烧糊涂级钳工”奖章说胡话:“轧钢机……传送带卡了……”楼道里15瓦的灯泡晃着油渍似的远处钢厂夜班吊机的轰鸣像头巨兽在咳楼上突然传来油锅爆炒的“滋啦”一滴冷透的菜油顺着墙缝滴下正砸在电路板我慌忙用袖口去劣质校服...
1987年冬,青州钢铁厂家属院我蜷在筒子楼外的垃圾堆旁,改锥捅进收音机后盖时,
手指关节冻得发紫。父亲躺在三楼那张嘎吱作响的铁架床上,右腿石膏里渗出黄褐色的脓。
昨晚他烧糊涂了,
级钳工”奖章说胡话:“轧钢机……传送带卡了……”楼道里15瓦的灯泡晃着油渍似的光,
远处钢厂夜班吊机的轰鸣像头巨兽在咳嗽。楼上突然传来油锅爆炒的“滋啦”声,
一滴冷透的菜油顺着墙缝滴下来,正砸在电路板上。我慌忙用袖口去擦,
劣质校服布料勾住一枚电容,“啪”地扯断了焊点。“陈远!面坨了!
”母亲的喊声劈开寒风。 我抓起螺丝刀往兜里一揣,起身时眼前发黑。饿的,
我知道——昨天那碗棒子面粥稀得能照见房梁裂缝。进家门时,
父亲正盯着墙上那面褪色的锦旗发呆。母亲把搪瓷碗推过来,清水挂面上漂着两片菜叶。
她左手无名指缺了一截,那是被纺织厂纺锤绞断的,缠着渗血的纱布。“刘主任明天来家访。
”母亲用筷子敲碗沿,“他说再听不见新闻联播,工伤补贴就……” 我咽下最后一口面汤,
摸出修好的收音机。旋钮转动时,隔壁王叔家传来摔酒瓶的响动。上个月他下岗后喝了农药,
洗胃回来那天,整栋楼都听见他媳妇的哭骂:“连死都不会挑地方!”1990年夏,
青州二中计算机房机箱风扇的嗡鸣声里,我闻到孙老师身上的樟脑丸味。他佝着背凑近屏幕,
酒瓶底眼镜几乎贴上CRT显示器:“这……真是你写的?
”十六行代码躺在绿色像素块组成的海洋里,像一串发光的咒语。
后排男生们的哄闹声潮水般退去,
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贪吃蛇的移动逻辑用了循环嵌套,
就是内存占用太高……”孙老师突然抓住我的手。他掌心滚烫,
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煤:“去北京!听见没?你该在硅谷和那帮洋人掰手腕!
”他塞给我一本《计算机世界》,雷军的签名龙飞凤舞地躺在扉页。窗外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冷汗把杂志边角洇软——昨晚父母的争吵在耳边炸响:“镯子当了能换八千!
小远上大学不要钱?”“那是娘临终前……”“可老陈的腿!”机房铁门“吱呀”一声,
扫地阿姨探进头:“小陈,该拖地了。” 我蹲着擦地时,在垃圾桶里翻到半本《无线电》。
第37页被人用红笔圈出一段:“磁铁干扰电路可重置老虎机程序”。1991年春,
光明街机厅虎哥叼着烟踹了我一脚:“小崽子,再碰机器剁你手!” 我缩在墙角,
左手掌新烫的伤疤还在渗血。三天前我在垃圾堆组装示波器,
偷接厂区路灯电力时被保安追打。
但此刻怀里的十七块三毛钱滚烫——那是我用磁铁重置老虎机赚的,
够买三本《计算机应用研究》。母亲发现钱时正在补袜子。她抄起擀面杖,
第一下砸在我背上:“偷的?抢的?” 第二下没落下来。她看见我摊开的杂志,
那些电路图被我用红笔勾得像血网。擀面杖“当啷”掉地,她突然抱住我发抖:“儿啊,
咱们穷死也不能脏了良心……”那晚我第一次失眠。父亲断断续续的呻吟声里,
我把十七块三毛钱折成纸船,塞进装外婆照片的饼干盒。1993年7月,
高考考场汗水把答题卡洇出波浪纹。最后一道大题题干明显出错,
我举手时监考老师斜睨我:“自己不会做就老实坐着!” 铃声响起时,
我蜷在座位上抽搐——连续36小时啃馒头复习,低血糖发作了。急救员掰开我紧攥的左手,
草稿纸上歪扭的字迹让他们发笑:“若f(x)在x=0处可导,
则左导数与右导数必须存在且相等……”三天后,钢厂医院消毒水味呛得我睁不开眼。
309病房门口,母亲的声音像绷到极致的钢丝:“……八级钳工的手,真没救了?
” 成绩单在裤兜里蜷成咸菜,723分的数字烙着大腿发烫。我转身撞上推药车,
玻璃瓶叮咣乱响。护士的白大褂掠过眼前时,
我突然想起考场那个荒诞的早晨——或许命运本就是道错题,除了硬解,别无他法。
1993年8月,青州黑市典当行的霓虹灯牌在雨夜里淌着血光。母亲跪坐在柜台前,
断裂的龙凤镯在放大镜下像条垂死的蛇。老板吐着烟圈:“镀金的?最多三千。
” “这是足金的!我娘临终前……”母亲的身影被雷声劈碎。我躲在对面邮局廊柱后,
看着母亲攥着铁盒冲进雨幕。摩托车灯刺破黑暗时,她像片枯叶被撞飞出去。
血水混着雨水蜿蜒到我脚边,她还在用身体护着铁盒,
嘴里呢喃着:“小远的学费……”那晚我在急诊室走廊刻代码。
手术灯将母亲的身影投在墙上,我掏出随身带的电路板,把镯子纹路转成二进制图案。
当护士喊“李秀兰家属”时,
机箱内侧已爬满01101110——这是“母亲”的ASCII码。1993年9月,
北上列车绿皮火车喷出的蒸汽糊在脸上,我紧了紧蛇皮袋的绳结。机箱棱角硌得胸口发疼,
那是母亲用血换来的长城0520,启动时会发出老牛喘气般的嗡鸣。硬座车厢里,
河南老农抱着面色青紫的女儿。孩子突然抽搐,我扯开长城0520的电源线。
电容放电的瞬间,车厢顶灯忽明忽暗,像在给死神打摩尔斯电码。“再来!
”我额头抵住车壁,指尖在键盘上翻飞。当女孩胸脯重新起伏时,
乘客们凑的684元救命钱被我塞进药盒。对面的眼镜男偷拍我,
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国青年报》记者。1993年9月,
清北大学宿舍穿皮尔卡丹的上海室友正踹他的IBM电脑:“册那!五千块买的!
” 我缩在门边,看他后脑勺翘起的发胶。机箱拆开的瞬间,
我摸到父亲工具箱里才有的温度——电容鼓包了,散热片积灰太厚。
重启成功的“滴”声响起时,他抛来的可乐罐砸中我肋骨:“牛逼啊!你这手活该去硅谷!
” 易拉罐拉环划破食指,血珠渗进键盘缝隙。我舔掉血渍,
铁锈味混着碳酸气泡在舌尖炸开。这一刻我才确信,那些蜷在垃圾堆旁修收音机的夜晚,
原来都是为了听见命运齿轮转动的声响。当夜,
中关村硅谷电脑城老板把二手CPU拍在桌上:“贴上这个标签,就是英特尔原装!
” 我摸着母亲寄来的腊肠,油脂渗进指缝。凌晨三点,我在BIOS里埋下报警程序。
工商局冲进来时,老板的巴掌还没落下,就被我手中的烙铁逼退。警笛声远去时,
我蹲在电脑城后巷呕吐。那个河南老农的女儿的脸突然浮现——她胸口除颤器留下的灼痕,
和我左手的伤疤一样,都是向世界讨要说法的印记。1994年春,
清北大学实验室我蹲在机房服务器后头,嚼着前天从食堂顺的冷馒头。
CRT显示器蓝光里浮着周慕云发来的邮件:“校财务系统防火墙已瘫痪,今晚十二点行动。
”键盘缝隙里还沾着干掉的血渍——昨天替教授修示波器时,我故意让电容爆浆,
换来这台386电脑的夜间使用权。母亲寄来的腊肠在抽屉里发霉,她不知道,
我啃了半个月馒头攒的钱,全喂给中关村黑市的盗版编程书。零点零三分,
我盯着屏幕上的绿色进度条。走廊传来保安的脚步声,汗珠顺着鼻尖砸在回车键上。
当“贫困生助学金发放记录.xls”弹出来时,我差点笑出声——刘建国,
校后勤主任侄子,月领三份特困补助。“你他妈疯了!”周慕云踹开机房门的瞬间,
警报器响了。我抱着主机箱跳窗,玻璃碴子扎进小腿也顾不上疼。
第二天全校通告“黑客入侵”,而刘主任家门口被贴满数据截图。
那晚我们在圆明园废墟上喝燕京啤酒,周慕云的金丝眼镜映着月光:“你代码里留了后门,
故意让IP被追踪?” 我没说话。母亲寄来的腊肠终于舍得拆开,
油脂在月光下像条琥珀色的河。1995年夏,金山软件研发部雷军的目光像X光机,
把我钉在会议室椅子上。
他手里攥着那封匿名信——我熬了三十个小时写的《WPS对抗Office的九种死法》。
空调冷气里,我听见自己脊椎咯吱作响。“陈同学。”他忽然把信折成纸飞机,
“知道为什么微软中国总裁年薪百万,却买不起中关村一个厕所吗?” 纸飞机扎进我胸口。
我咽下带血丝的唾沫——为赶这封“求职信”,我吞了半管酒店过期牙膏充饥。雷军站起来,
袖口露出精钢表链:“给你三个月,让WPS能打开.doc文件。
” 我攥紧兜里的电路板,边缘割破掌心。那是用外婆镯子残片改的U盘,
存着母亲化疗的CT报告。1996年冬,西翠路出租屋暖气片嘶嘶漏着水,
我蜷在二手冰箱和床板的缝隙里敲代码。显示屏上爬满蠕虫状的字符,
像母亲化疗后脱落的头发。周慕云踹门进来时,
我正在给静脉曲张的小腿放血——久坐引发的血栓,放点血就能继续工作。
他甩给我一沓文件:“雷军要把你调去杀毒软件部,明天签合同。
”我盯着《股权分配协议》右下角的数字,突然笑出声。窗外积雪压断枯枝,
像极了我掰断父亲那枚“八级钳工”奖章的声音。“他们要的不是技术,是条看门狗。
”我把协议扔进煮泡面的小锅,火苗窜起时照见周慕云抽搐的嘴角,
“知道我怎么攻破校财务系统吗?在代码里埋了个‘寡妇’——只要有人删改数据,
就会向纪委邮箱自动发信。”周慕云走时把门摔得震天响。
我继续啃生胡萝卜——牙龈出血太严重,热食都咽不下去。凌晨三点,
当WPS终于吐出第一份.doc文档时,显示屏上的微软logo像道流血的伤口。
1997年秋,人民医院走廊呼吸机的声音像台老式打印机。我跪在ICU门口,
膝盖压着连夜写的《宏病毒专杀工具源码》。护士第三次催缴费时,我掏出裤兜里的小刀。
“抽600CC。”我扯开衬衫纽扣,“O型血,新鲜。
” 血贩子捏着我胳膊打量:“学生仔?给你加五十。” 装血的塑料袋温热如活物,
换来的三千六百块刚好够一天ICU费用。我蜷在厕所隔间啃葡萄糖粉时,
雷军的电话来了:“微软开价百万挖你。”走廊灯光忽明忽暗,
我盯着采血针眼:“能预支五年工资吗?”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明早十点,
带公章来签对赌协议。”1998年春,西苑殡仪馆骨灰盒太凉,
我把它裹在写满代码的草稿纸里。周慕云递来黑伞时,
我嗅到他袖口的古龙水味——这孙子现在给微软当技术顾问。“你知道癌细胞转移有多快吗?
”我摸着骨灰盒上的裂纹,“比我的代码快十倍。” 雨砸在伞面上像加密电报。
周慕云突然说:“雷军把你的对赌协议卖给了投资人,
现在整个中关村都知道你欠金山两百万。”殡仪馆后墙贴着“金山毒霸”的海报,
我的照片被P成西装革履的笑脸。母亲临终前的话突然在耳蜗里炸响:“儿啊,
别学你爹……”我把骨灰盒塞给周慕云,冲进雨里。长安街的霓虹灯在泪眼里晕成血色,
雷军的劳斯莱斯从我身边驶过时,我正把“金山软件总监”的工作证塞进垃圾桶。当夜,
中关村电子市场我踹开“宏达软件”的玻璃门时,虎哥正在数钱。十年过去,
他脸上的刀疤更狰狞了:“哟,这不是钢厂修收音机的小崽子?
”486电脑在身后嗡嗡作响。我甩出沾着骨灰的U盘:“《盘古中文办公系统》源码,
换五十万现金。” 他腮帮子上的肉抽了抽:“去年有个清华教授卖这个,
被我剁了三根手指。” 我抓起键盘砸向防盗摄像头,液晶碎片四溅:“要么现在交易,
要么我往你每台盗版盘里种病毒——专删毛片那种。”凌晨四点,
我抱着装满现金的肯德基全家桶站在天桥上。
对面金山大厦的LED屏闪烁着“民族软件之光”,我扯开衬衫,让雨点砸在胸口的伤疤上。
那些母亲化疗留下的数据线图,此刻像极了未完成的代码。1999年冬,
华强北赛格大厦我蹲在厕所隔间里数钱,肯德基全家桶的炸鸡味混着隔壁传来的屎尿臭。
卷帘门外,潮汕老板的吼声震得天花板掉灰:“扑街!联发科芯片又涨价!
”裤兜里的Nokia 5110震起来,是周慕云。我按下接听键,
听见他背景音里的机场广播:“雷军要投三百万买你手上那批翻新机。”“告诉他,
我改行卖骨灰盒了。”我把手机贴在蹲坑边缘,冲水声盖住他后半句话。
箱上摊着电路图——这是我从二手BP机里拆出的灵感:把联发科MTK芯片塞进手机主板,
再套个清华同方的壳。山寨作坊的老林蹲在旁边抽烟,
烟灰落在图纸的射频模块上:“后生仔,你这方案要烧主板的。
”我抓起热风枪捅进他怀里:“烧不起来,我帮你把债主引到海关。”2000年春,
白石洲城中村天台铁皮屋在台风里摇晃,像台即将散架的服务器。阿May把泡面端来时,
显示器正蓝屏——这是她第七次偷接隔壁理发店的电。“陈总,
展讯的人说要告我们抄袭……”她马尾辫上的红绳让我晃神,
像极了母亲当年断镯上的红绒布。我踹开窗,
让暴雨浇在发烫的机箱上:“把GSM模块频率调高0.3MHz,专利书里没这个参数。
”二十台拼装机在墙角闪烁,像群电子萤火虫。三天后,
当这些“星辰1代”手机在罗湖口岸被疯抢时,我在海关监控室里啃冷掉的叉烧包。
屏幕上的走私车燃烧成火球,老林在电话里尖叫:“条子抄了产线!”我抹掉嘴角油渍,
给雷军回短信:“三百万不够烧,我要三千万。”2002年夏,
香港红磡仓库周慕云的金丝眼镜映着集装箱的锈迹:“高通的人明天到,
你确定要骗他们喝工业酒精?”我拧开茅台瓶盖,
把二锅头灌进去:“去年他们的专利费抽走我62%利润。”酒局设在维港游轮上。
当高通副总瘫在真皮沙发里吐胆汁时,我扒下他的劳力士:“告诉你们CEO,
下次来深圳记得买医保。”凌晨三点,我在尖沙咀码头呕吐。阿May突然出现,
高跟鞋踩碎我的影子:“税务局的在查你离岸账户。”海浪把月亮撕成碎片,
我拽过她手里的爱马仕包,掏出瑞士军刀划开夹层——微型窃听器闪着绿光。
“你爸欠高利贷的钱,我早还清了。”我把窃听器扔进海里,“告诉那帮孙子,
星辰科技明天就注册巴拿马壳公司。”200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