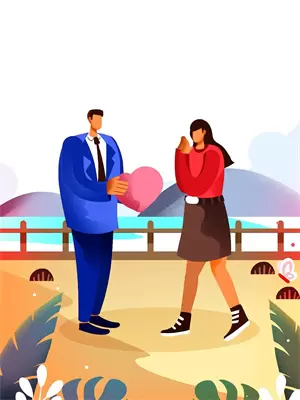翻开此页,每字撕裂心秘,命运极限对决启幕!1我出生那晚,雷雨交加,像是天塌了一角。
娘疼得昏死过去,父亲抱着我,满脸都是雨水和汗。他的眼神惊惶不定,像是在害怕什么。
门外的风透过破旧的木窗灌进来,吹得油灯摇曳不定,
火光映出一张张面色煞白的脸——爷爷跪在地上,嘴里不停念着晦涩的咒语,奶奶拄着拐杖,
死死盯着门外,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桃木剑。“它来了。”奶奶的声音像是被撕裂的布,
沙哑又沉重。门外,一双鲜红色的绣鞋缓缓踩进泥水里。啪嗒,啪嗒。鞋子沾上了泥,
沾上了血,雨水冲刷过鞋面的瞬间,竟渗出了浓稠的暗红色液体,一点一点,滴落在门槛上。
父亲的呼吸猛地一滞,猛然抱紧了我,喉头发出一声难以察觉的哽咽。
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的女人站在雨幕里。她身材纤细,
头上罩着红盖头,衣摆被大雨浸湿,贴在苍白得不像人色的脚踝上。她没有五官,
脸上光秃秃的一片,唯有腮边一点朱砂红,像是笑着,又像是哭着。她静静地看着我。
我才刚出生,嘴里还含着血腥味,尚且不会言语,却在那一瞬间,感到从骨子里涌出的恐惧。
她缓缓抬起手,手腕又细又白,像是没有血色的瓷器,手里捏着一张发黄的婚书。
婚书上湿漉漉的,字迹斑驳,墨迹被雨水浸透,却仍能看清上面的字:“此女,吾妻。
”父亲的身体僵硬如铁,额角冷汗涔涔,他一动不敢动。奶奶厉喝一声,
拐杖狠狠跺地:“滚!”红衣新娘没有动,她只是慢慢地,将手里的婚书放在供桌上,
指尖划过上面的名字,缓缓地,又写上了一道血红色的痕迹。像是盖上了契约的印记。
“是你自己惹下的孽!”奶奶声音尖锐,像是在嘶吼,“你当年不该杀那只狐狸!
”她话音刚落,父亲的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几乎要把我捏碎,
我在襁褓里轻轻抽泣了一声,他才猛地松开,脸上写满了痛苦和悔意。
“那只狐狸……是我狩猎时误杀的。”他嗓音干涩,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这句话,
“当年它刚生完崽,奄奄一息,被我一箭射穿了脖子……我本以为只是寻常野兽,
没想到……没想到……”他喉咙滚动,像是吞下了一块烫石,眼神死死盯着婚书上的字,
瞳孔紧缩。“它的崽子还活着。”奶奶冷冷道,“它长大了,来找你报仇了。
”屋外的风瞬间灌进来,烛火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投出新娘扭曲的影子。她不说话,
只是微微歪着头,像是在欣赏我们恐惧的模样。雨越下越大,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狂风中剧烈摇晃,树枝“咯吱”作响,像是随时会断裂。
红衣新娘忽然笑了。她没有嘴,可我听见了她的笑声,那声音从四面八方钻入耳朵,
带着阴冷的潮气,像是雨水倒灌进喉咙,让人窒息。父亲猛地抱着我后退:“娘,怎么办?
”奶奶的手死死握着拐杖,骨节发白,眼里浮现出挣扎和痛苦。“把她送出去。”她低声道,
“送去山神庙,做替死鬼。”父亲瞪大了眼睛,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一夜,
我被裹进湿漉漉的襁褓里,放进了一个破旧的竹篮里,送到山神庙。
庙里只有一座破败的神像,脸上的漆已经剥落,隐隐露出底下模糊的木纹。
我被轻轻放在神像前,身下垫着一张黄符,符咒上血迹未干,隐隐渗入我的皮肤。
奶奶跪在神像前,低低地念着什么。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可风却更冷了。四周静得可怕,
连虫鸣声都没有。突然,我听见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啪嗒,啪嗒。
像是有人赤脚踩在潮湿的地面上。奶奶的身体一僵,猛地抬头。神像前,红衣新娘站在那里,
盖头不知何时已经被掀开,露出了一张极度模糊的脸,仿佛是雾气凝成的,没有五官,
却在无声地看着我。她伸出手,苍白如玉的指尖缓缓抚上我的脸,触感冰冷,像是死人。
奶奶猛地咬破舌尖,吐出一口血,急促地念起咒语。黄符上的血光陡然亮起,
新娘的手指瞬间被灼烧得冒出黑烟,她缓缓低头,看了一眼指尖焦黑的痕迹,
幽幽地叹了口气。然后,她笑了。“既然你们不愿意……”她的声音空灵得像是从远方传来,
带着轻微的回音,“那就换个方式。”她抬手一挥,破庙里的烛火瞬间熄灭,
四周陷入死一般的黑暗。我听见奶奶的惊呼,听见父亲的呜咽,听见夜风呼啸而过的声音。
然后——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了我的额头上。带着淡淡的腥味。是血。
新娘的脸在黑暗中浮现,她缓缓俯身,贴近我的耳边,轻声呢喃:“小娘子,我们来日方长。
”2十岁那年,夜风裹挟着腥湿的寒意,钻进我的脖颈。槐树下,奶奶拄着拐杖,
苍老的手攥紧了那把桃木剑,手背上青筋暴起,像是盘踞的蚯蚓。
她的目光紧紧锁在树梢——那里盘踞着一只通体雪白的狐狸,尾巴垂落在树枝间,晃晃悠悠,
像是一缕缠绕的雾气。它静静地俯视着我,幽蓝的瞳孔在夜色里微微发光,如同两点寒星,
冷冽而克制。“从今日起——”奶奶咬着牙,一字一句地对我道,“你要用你的命,
换回你爹当年的杀孽。”我脚下的泥土潮湿又冰冷,雨水还未彻底渗透进土里,
空气中弥漫着霉腐的气味。我垂在身侧的手指不受控制地蜷缩,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却没有出声。狐狸缓缓俯身,贴近了我一些。它的喉间滚出一声极轻的低吟,
像是某种古老的叹息。“借命还命。”它说,声音竟透着一丝温柔。可这份温柔,
却让我头皮发麻。奶奶用力推了我一把,我踉跄几步,跌倒在湿漉漉的地上,手掌摔得生疼。
狐狸就在我面前,近得能看清它鼻尖上细小的水珠,能闻到它身上淡淡的木质香气,
像是雨后的松木。“拜它为师。”奶奶低声催促。我一动不动,嘴唇发白。
狐狸的尾巴轻轻扫过地面,眯了眯眼:“怕什么?你身上早已经沾满我的气息,不拜,
活不过十五岁。”它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陈述事实。奶奶死死盯着我,
眼里没有丝毫迟疑:“拜下去。”我死死咬住唇,心里抵抗得厉害。
可当目光触及奶奶攥着拐杖的手,和她隐隐透露出的焦急时,我终于缓缓屈膝,
膝盖磕在湿泥里,凉意沿着骨头攀爬而上。我磕了三个头。狐狸收回视线,似乎很满意。
它的尾巴一卷,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那一瞬间,一股灼热的气息猛地钻入我的皮肤,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血液里燃烧。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狐狸轻笑了一声。“这道印记,
能保你活命。”它的声音轻得像是风,“但若违誓,印记反噬,你死,父母性命不保。
”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成为奶奶的继承人。她教我怎么画符,教我如何驱邪,
也教我如何与“它们”交涉。“神婆不只是请神,也是送鬼。”奶奶握着毛笔,蘸了蘸朱砂,
目光幽深,“你要明白,世上最难惹的,不是人,是念头。”我低头描着符纸,手心渗满汗。
窗外的月光惨白,透过破旧的窗纸洒进来,映出屋角供台上的那只白瓷狐狸像。
它眼尾一点朱砂红,仿佛活物,在静静地凝视着我。我不喜欢它。它总让我想起那夜,
那只站在槐树上的狐狸,以及它幽蓝色的眼。奶奶察觉了我的走神,
忽然叹了口气:“你在怕它。”我不说话。“没用的,孩子。”她淡淡道,“你是借命之人,
怕,是没有意义的。”“借命?”我咬紧牙关,“那我的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
”奶奶的目光沉了几分,像是被我问住了。良久,她才缓缓地开口:“人活一世,
很多东西从出生起就注定了,躲不了。”我没有再问。但心底那股隐隐的不甘,
像是一颗种子,在潮湿的泥土里悄然生根。三年后,村里开始接连不断地死小孩。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暴毙,死状骇人,他们的皮被剥掉,眼睛被挖走,尸体被丢在村头,
像是被什么东西啃噬过,惨不忍睹。全村人慌了。“是不是妖怪害的?
”“是不是哪家冲撞了狐神?”“是不是……”他们的声音压低了,
最终汇成了一个恐怖的结论——“是不是她?”目光纷纷投向了我。站在庙门前的我,
被一双双仇恨与恐惧交织的眼神包围。他们害怕,却又贪婪地渴望一个能推卸罪责的对象,
而我,刚好是最好的替罪羊。“是她!她从小就和妖狐有牵连,狐神要带她走,
我们却留着她,所以孩子才死了!”有人恶狠狠地喊。“对!把她献祭给狐神!
”人群开始沸腾。有人举起了锄头,有人捡起了石头,更多的人开始怒目而视,
嘴里嘟囔着难听的话。奶奶挡在我面前,声音冷厉:“她是神婆的继承人,若她死了,